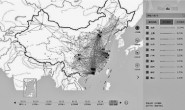过去四十年的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境况。我们能够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维度对这一巨变进行分析,比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政策在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通过崭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巨变进行直观把握。在当下的历史-地理节点上,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将新的城市经验与既往经验完全切割开来——毕竟,重工业立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连同那时捉襟见肘的城市生活一起。但是历史的延续并没有被空间的巨变所彻底掩盖,在新的城市经验的很多维度上,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既往城市经验/政策的影子。
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维度便是旷日持久且日趋激化的城市人口调控问题。与计划经济时代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不同,进入城市的大量所谓“流动人口”构成了最近四十年城市巨变的核心推动力,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却屡屡遭遇名目繁多的“调控”和阻力,并由此而引致了王春光归纳的“半城市化”现象。在这个维度上展开的最新案例来自北京。2017年11月,在北京市大兴区一场夺去了19条生命的大火之后不久,北京市政府便迅速展开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并在事实上促成了对“流动人口”的大规模驱赶 。这个行动的语境是已持续了数年的“非首都功能疏解” 和“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而它的催化剂则是事件发生两个月前获得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其中规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在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范畴内,对“流动人口”及户籍制度等相关话题的讨论已经相当丰富。在早期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所做的研究的基础上,目前的主流观点已经注意到歧视性制度所造就的本质化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我们转换分析视角,通过过程化的公民权概念来实践“承认的政治”。在近期一项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调查中,杨菊华发现流动人口总体融入水平仍然不高,并且“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程度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广义的制度约束(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是如何限定“流动人口”的城市经验的,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些制度约束背后又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
毋庸讳言,前述一系列调控人口的政策/制度本质上都是城市政策,它们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按照某种默认的城市观念重新进行社会空间排序(socio-spatial reordering)。在城市观念和社会排斥实践之间,空间变成了具有媒介作用的关键词,并因而可望成为我们理解制度逻辑的一个切入点。但空间应该如何定义和分析呢?在人文地理学文献中,对空间的界定多样并且动态,几乎无法穷举 ,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空间与社会是相互形塑的,作为社会过程的中介物(intermediary),空间也同时被社会过程塑造和重塑,因而内蕴着政治性 。在多琳·马西 看来,空间概念和内涵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对应着政治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所以我们思考空间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对政治问题的探究和对新的社会过程的构想。
把空间放置在分析框架的核心位置,我们便可以从可见的(visible)城市变迁出发,去探索城市政策的主体(subject)及其能动性(agency),进而借助空间视角对制度逻辑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在人口调控问题上,空间的在场突出体现在那种默认的城市观念上:到底何为城市、何为首都?为何特定的产业可以被归类为“非首都功能”并加以疏解?为何城市的总人口要施加如此严格的上限?除了语焉不详且争议颇多的水资源限制这个理由外,我们至今依然不清楚,指引着这些政策制定的理想城市状态是什么模样。这个默认的城市观念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空间想象,但是它与城市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勾连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知识与权力联结的过程中,空间图绘(mapping space)在话语层面合理化了特定的知识,从而服务了特定的权力机制 。
通过分析空间想象与社会过程(尤其是人口调控过程)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地理动态,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城市时代的意识形态,构想和实践别样的城市空间,从而更有效地争取并重构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这一分析要求我们同时推进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将城市议题空间化,在空间的维度思考和反思社会实践和政治经济框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将这一空间机制历史化,通过融入时间性的视角来识别空间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惯性和断裂。为了同时关照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我在这篇文章里将借助福柯的谱系学方法 去解析当下城市境况的意识形态动态——具体来说,我将讨论官方城市观念背后的空间图绘是如何生成和演变的,以及它的断裂和延续反过来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与政策,最终不断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反城市主义”:概念与脉络
在引言中已经提到,目前对待大城市的官方态度(以及相关的规划、方针和政策)是受着一种默认的城市观念指引的,那么这个观念——或者说是绘制空间的话语——是什么呢?为了更好地界定它,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视野,在更广大的地理和历史语境中搜寻答案。在一篇发表于1976年的文章中,旅美地理学家马润潮总结了当时中国的“反城市主义”政策 。通过对中国半殖民地历史和革命历程的介绍,以及“下放”和“上山下乡”政策的梳理,他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策略事实上建立在反城市(anti-urban)的基础上。一方面,工业发展过程中要求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事实上严格控制和阻止了城市空间本身的扩张;另一方面,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方针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向农村转移城市资源(其中包括知识青年等人力资源)而得以推进。“反城市主义”这个概念由此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城市和现代性在社会学研究传统里常常是成对出现的概念。比如,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将大城市中人们情感生活的紧张归咎于从劳动分工和现代文明中日益发展出来的一种精神 (geist),这种精神遵从市场原则,受一种理性计算的经济利己主义(economic egoism) 支配,将人的个性贬低得毫无价值。最终,现代文化中的客观精神压制了主体性,作为个体的人也被化约为了可被量化的“客观”的存在 。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斯继承和发展了齐美尔的观点,他在后者描述的城市个性的精神分裂(schizoid)特征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支撑城市主义理论(a theory of urbanism) 的三个基本属性:人口规模膨胀,高密度社区,以及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异质性 。与齐美尔不同,沃斯并没有对这种城市主义的状况进行规范性评价,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新的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物理结构、生态秩序、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个性的集合——换言之,城市主义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个体性被劳动分工化解为诸种范畴、“均质人”(average person)的诞生等社会现实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激起的若干浪花。
如果说沃斯的生活方式论为二十世纪早期对城市主义的社会学探索设定了一个规范议程,那么齐美尔的担忧与愤懑则更加接近“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态度。迈克尔·汤普森将这一观念/态度界定为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保守反应:面对被城市空间加剧的原子化和失序生活,人们开始探索别种空间资源以拒斥现代形式的生活和意识,并由此而构建起有别于城市主义的情感意识、生活形式和社会联结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对道德自我(moral self) 的追寻常借用非城市 (nonurban) 的生活形式和传统道德信条加以表征,并通过特定的空间过程进行实践。“反城市主义”观念最常见的话语表达是对田园牧歌的怀旧式追忆,这在罗伯特·博勒加德对美国郊区状况的历史考察中有着鲜明的呈现 。在他看来,托马斯·杰斐逊可被称作美国的第一个“反城市主义”者,后者在写作中对大型聚落始终抱持怀疑和警惕态度,认为工业化和资本竞争不仅会伤害农业社会的根基,而且最终会导致自由的败坏。这一立场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城市郊区的迷思:作为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郊区可以被发展成为所谓田园城市(garden city),从而能够兼容城市生活与个体之中内蕴的保守价值。但是最终,与郊区兴起相伴随的是美国内城的衰落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状态 ,而面向郊区的逃遁也只是讽刺性地造就了一种千篇一律的低档建成环境,在那里的人们发现自己再也无处可逃。
但田园牧歌和郊区化并非“反城市主义”唯一的话语表达和空间机制。汤普森注意到,虽然“反城市主义”这一意识的起点是对自然(natural)和人工(artificial)所做的区分,但是它的焦点和具体表现随着历史和地理境况而不断变化,并因此产生了多样且动态的政治效果。换句话说,“人类思想和行动事实上是镶嵌于(embedded)空间之中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思想和意识的主体间属性(intersubjective nature)受制于空间与社会联结状态(association)之间的关系及其属性” 。为了理解中国的城市和人口调控状况,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发问,马润潮在1976年揭示的那种社会主义“反城市”策略受制于什么样的空间和社会联结状态?这一策略经过什么样的机制才终于把阴影投向了当下的城市过程?面对这一问题,前述社会学传统的不足立刻凸显:他们通常将“反城市主义”等价于对城市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反动,却忽视了一支在相反的、革命的方向扛起“反城市”大旗的力量: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城市》一书中,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城市观念做了精彩的述评 。通过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城市实在(urban reality)的段落,列斐伏尔发现城市状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后者那里,一国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工、商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区分,这进一步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 。立足于这个论断,列斐伏尔回顾了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城乡关系之演变,然后在这一历史主义框架中推出了他自己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哲学一般性上的抽象论断,而是建基于对欧洲当时被忽视的城市历史的重新发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生产出了历史的能动性,并成为历史的主体(the subject of history): 一方面,城市生产了诸多物品(“生产”的狭义层面);另一方面,城市生产了工作,观念,语言,灵性(spirituality) 等一切构成了社会与文明的事物(“生产”的广义层面) 。正是在城市中,资源、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愉悦得到前所未有的聚集,市政管理、警察、税收等事务(municipality)成为必需,作为整体的政治成为可能,劳动分工被进一步推进,并造成了广泛的异化和阶级的生成——这所有要素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纲领和行动的前奏 。
但是城市在他们的革命纲领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却是完全负面的: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城市被视作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为什么会这样?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短地回顾恩格斯在工业革命时代切身经历的城市问题(马克思对城市经验的论述则相对有限)。1845年,青年恩格斯根据他在英国城市(以曼彻斯特为主)的见闻写就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尝试着通过对城市状况的勾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性质 。面对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贫民窟之间鲜明的对比,无比震惊的恩格斯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造就了资本和人口的高度集聚,不仅导致了恶劣的城市环境,而且通过“竞争”的话语促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st all) 的社会战争(social war)。列斐伏尔总结道,城市空间在恩格斯那里被视作一个压迫的空间——资本主义秩序(order)导致了城市状况的混乱(chaos),反过来又用种种空间手段对贫穷和混乱加以分隔和掩盖。换言之,原子化、异化、贫困、空间区隔——这一系列城市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资本主义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引致的人口集聚和城乡分割。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城市人口调控的逻辑:反城市主义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