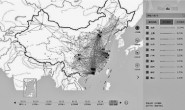(三)行政级别越高的政区调整频率越低
从新中国70多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来看,国家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三类省级行政区调整频率最低,且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在1988年和1997年出现两次零星调整,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主体架构。相比于省级政区, 国家对地级政区的调整更加频繁。以改革开放后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1978—2019 年全国撤地设市、地市合并和县市升格这三种区划调整方式一共发生了267次,调整频率显著高于省级行政区。而对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等县级行政区划来说,其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频率比地级政区更高。以改革开放后为例,1978—2019年全国范围内通过撤县设市和切块设市形成县级 市473个,县市合并发生38次;通过撤县(市)设区和切块设区形成市辖区 429 个,发生区界重组270次(见表1)。如果再算上县市之间的微调等情况,县级政区的区划调整频次会更高。至于乡镇级行政区,其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频率则更为频繁,从图4可以看出,1978—2019年全国建制镇数量增加了18020个,但期间除了发生撤乡设镇之外,同时还发生了会使建制镇数量减少的大规模的乡镇撤并和撤乡设街道办等调整,可见乡镇级政区在这期间经历的调整次数非常多,远远高于县级政区的调整次数。出现政区调整频率随行政级别降低而增加的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行政建制的变革必然会打乱原有的社会管理秩序与体制, 影响社会的稳定, 政区行政级别越高,调整后所带来的影响越大,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地区,越不会轻易变动其行政建制。
(四)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
70多年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逐步从宏观尺度转向微观尺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是构建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此时区划调整主要针对的是国家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内容是划分省域空间,区划调整尺度很大。改革开放后,省级行政区划基本已经尘埃落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税制改革为代表的分权化改革的推行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完善地级政区的权力配置和空间重构是行政区划调整的新的重点。从表1和图2可以看出,1978年之后中国的地级政区调整一共进行了267次,其中255次都发生在1978—2003年,地级市总数在2003年后也基本保持不变。可以说地级市的调整在2003年左右基本告一段落。地级市做实的同时,县级市和市辖区也在快速增加,县级市增加在经历了一个高峰之后被人为叫停,而市辖区则一直处于优化调整之中,成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对象。而随着2017年以来撤县设市的重启,县级行政区将继续成为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对象。此外,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改革不断推进,乡镇级政区的区划调整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科学合理规范地实施撤乡设镇和乡镇撤并,能有助于乡村振兴和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乡镇社会治理格局,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将不断缩小,区划管理也将越来越精细化。
(五)行政层级调整趋向扁平化
70多年间,中国地方行政层级调整的焦点集中在省和县之间有没有增设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具体来看,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地方行政层级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1952年之前以“大行政区—省—县—乡”四级制为主;1955—1966年以“省—县—乡”三级制为主;1967—1978年以“省—地区—县—人民公社”四级制为主;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全面推行之后以“省—市—县—乡”四级制为主。进入 21 世纪后,出于对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提高地方行政管理效率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考虑,国家开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试点。自2005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改革。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不少省份积极响应,在省内区位条件好、经济实力强、城市化水平高的县域进行省直管县试点。因此,国内现已有部分地区建立起“省—市(县)—乡”三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由此可见,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当前呈现出行政层级扁平化的趋势。
四、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的展望
步入新时代后,中国面临着两大重任,即在国内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的行政区划工作应紧紧围绕这两个任务展开,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规划布局,这是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的最基本要求。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应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完善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
长期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在 2019 年之前,中国开展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主要参考依据一直是 1985 年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虽然该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为国家加强行政区划管理和保持行政区划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它已经难以满足行政区划管理的实际需要。针对行政区划管理领域过去长期存在的随意性大、规范性不强、审批后落实不力以及违规追责机制缺失等问题,2018年国务院出台了《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对行政区划管理的原则与方针、变更程序与权限、设置与标准、监督与管理以及追责机制做出了具体、系统的规定,提高了行政区划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但是新时代行政区划管理工作仅仅依靠这一部法规是不够的。在当 前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中,对撤县设市、撤县(市) 设区、撤镇设街道办等行政区域调整事项的标准与程序的立法均不够完善。因此,必须对行政区划法治建设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从宪法等国家基本法的层面,不断完善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设置。
(二)完善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
当前,中国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缺乏市辖区设置标准。新中国成立至今,虽然市镇设置标准有过多次变更,但是国家一直没有出台专门的市辖区设置标准。2014年民政部起草了《市辖区设置标准(征求意见稿)》,然而至今没有出台正式文件。由前文所述可知,当前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正在逐渐缩小,市辖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结构,将成为新时代政区调整的重要对象。市辖区设置标准的缺失将严重影响未来行政区划调整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必须尽快得到完善。二是设市标准过于单一。当前,第二轮撤县设市正在拉开帷幕,为了慎重提出与审批撤县设市申请,避免再次一哄而上,需要进一步规范设市标准。尤其是,由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与轨迹存在较大区别,设市标准必须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类型的区域。在新时代,中国的区划调整工作应在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这两点不足,抓紧研究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早日建立起科学、系统、完整、便于操作的城镇型政区设置标准的体系。
(三)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设市的主要模式是撤县设市。但是,一种设市模式很难适应中国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的城市化发展需要,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是唯一出路。〔17〕目前,中国存在很多特大镇,这些镇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面均已具备了设市条件,但却无法直接设市。为协调特大镇行政建制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矛盾,撤镇设市是一项顺应城市化进程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特大镇设市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切块设市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县辖市”模式并不合法,特大镇想要顺利设市,势必要探索出一条新路子。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个别地区已经试行了撤镇设市,例如1987年福建省石狮镇改市和199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镇改市,这些案例为之后更加广泛的撤镇设市积累了宝贵经验。2019 年,国务院批准浙江省龙港镇改市,龙港成为新中国首个不设乡镇和街道的县级市。龙港镇改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积极探索特大镇设市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同时也预示着新时代中国的城市设置将会出现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四)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评估机制
对于任何一项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而言,事前的调研论证与事中、事后的效果评估都是必不可少的。事前论证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事中评估则可以及时发现、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保证执行过程中不出现偏差。而事后评估是在区划调整方案实施后的一段时期内对行政区划调整的效应与效益进行科学评估,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对之前的调整目标是否实现进行评价,并总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更好地推动之后的行政区划工作而积累经验。当前,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整体上缺乏系统、有效的评估机制。行政区划调整前,对调整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的评估还不够充分。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和调整完成后的效果评估机制尚未建立,不能确定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很难为之后的行政区划管理积累经验。因此,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评估机制,不断完善行政区划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五)明确行政区划管理的主体并赋予其必要的权威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行政区划界线消失或模糊、行政区之间矛盾与冲突加剧等问题,均与行政区划管理机构的权威性不足有关,主要体现在规划与建设部门在涉及跨行政区土地规划与建设时没有征得民政部门的同意,即国家和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与建设部门在制定重要职能单位布局规划与建设决策前没有征求并考虑行政区划主管部门的意见。一个职能单位跨区域建设后, 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单位,如民政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安局等部门,不得不围绕如何解决这个单位跨区域占地导致的诸多矛盾而开展多方协调工作,这造成了巨大的行政资源浪费。许多年的实践表明,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局、住建委在规划与建设过程中不考虑行政区域界线,既给行政区划管理部门造成了管理困难,也妨碍了重要职能单位的自身发展。在这些困难与难题中,有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有些问题虽然找到了解决办法,但都是被动的、事后的和临时性的,即在建设后被动地调整行政区划或设立新的临时管理机构。这些办法不仅不能完全解决跨界建设所造成的管理问题,而且有可能造成新机构不断出现、行政区域间利益冲突固化等新的问题。建立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局、建设部门与民政部门的多方会签制度,是事先、主动解决重要职能单位跨界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作者:张可云、李晨 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注:
①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正式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②见1984年11月22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的通知》。
③这一原则是在2017年12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
〔参考文献〕
〔1〕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页。
〔2〕〔5〕〔9〕田穗生、罗辉、曾伟:《中国行政区划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1、146、108页。
〔3〕朱建华、陈田、王开泳、戚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地理研究》2015年第2期。
〔4〕王开泳、陈田、刘毅:《“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理论创新与应用》,《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
〔6〕〔13〕吴金群、廖超超等:《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40年》,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0-72、202-203页。
〔7〕李金龙、苏妮娜:《行政区划体制三次变迁及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启示》,《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3期。
〔8〕汪宇明:《中国市管县(市)体制的区域结构关系及发展趋势》,《经济地理》2000年第3期。
〔10〕范毅、冯奎:《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化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6期。
〔11〕魏后凯、白联磊:《中国城市市辖区设置和发展评价研究》,《开发研究》2015年第1期。
〔12〕殷洁、罗小龙:《从撤县设区到区界重组——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城市规划》2013年第6期。
〔14〕薄贵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
〔15〕马春笋、张可云:《我国行政区划基本问题与走向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
〔16〕王开泳、陈田:《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
〔17〕魏衡、魏清泉、曹天艳、赵静:《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人文地理》2009年第6期。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