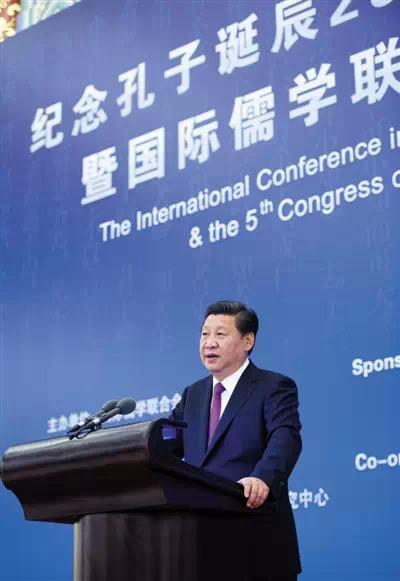儒家转型与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
恐怕没有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表示满意,不论是最狭窄、也最亲密的家庭伦理,还是居于中间层面的职业伦理,抑或包括政治在内的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公共伦理。事实上,很多人相信,我们恐怕生活在相当严重的道德荒漠、伦理真空的状态。商人之欺诈、医生之堕落、官员之贪腐,在在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剥极而复”,不少人已经形成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意识。具有这种道德伦理重建意识的人们立刻联想到了古老的儒家,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教化的主要力量就是儒家——尽管在现代这一事实给儒家招来了批评。但今天我们要严肃应对的其实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儒家能够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重建发挥正面作用吗?
儒家经典的道德教化形态
在西方,道德伦理教化借助组织化的教会体系进行。儒家即便可被当成宗教对待,它也只是美籍学者杨庆所说的“分散型宗教”,不存在一个有形的宗教组织体系。在儒家那里,哲学与宗教是合一的,两者结合于儒者共同体的知识与道德实践活动中。学识程度不等的儒生承担着对社会进行伦理教化的职能——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是社会进行自我伦理教化的助推器。
虽然儒家没有教会组织体系,但从汉代以来,儒家逐渐改造了社会,也构造了其发挥教化功能的至少三种世俗的社会文化制度:
第一,在最普通也最普遍的层面上是家庭、家族组织。接受过儒家教育的人士作为父亲、儿子、兄弟,遵循儒家礼仪规范,积累而成儒家化的习俗、礼俗,维持着社会的基础性秩序,并在家族内部提供公共品。
第二,同样是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在家族之外也创造出种种社会组织,包括慈善公益组织、同业公会组织(尽管他们经常依赖民间信仰保持其凝聚力)。这些组织在陌生人中间提供某些公共品,并维系着家族之外的伦理秩序。
第三,士人通过讲学、以文会友,借助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复杂交往形态,形成一个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士人共同体,这种士人共同体的覆盖范围有时非常广泛,甚至形成全国性共同体。在此共同体内,具有较高儒家知识水准的士人与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官员相互激励,维持精英群体内部的伦理规范。这个共同体的道德自觉,也是公共生活保持良好秩序的前提。
最后一个对于社会的教化体系是最为重要的。这与儒家道德伦理论说的内在逻辑有关。孟子断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儒家相信,良心、道德感内在于人性之中,凡是人都具有“善端”、“善根”,或者说善的潜能、可能性、内在倾向。所以儒家乐观地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这里蕴含着伟大的平等思想。
但孟子那段话最后一个关键字“思”却引出一个大问题。所有人固然皆有善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的善行相等。孟子的解释是:因为不同的人的“思”的能力不同。孟子接下来说:“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大人、小人或者君子、小人之分,也就因此而产生,《孟子·告子章句上》有一段对话: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因此,尽管人皆可以成尧舜,百姓于日用而不觉之中的行为依然可以是善的;但他们也完全有可能蔽于物欲,随波逐流,作恶(至少是不行善)而不知。如果人们普遍处于这种自然状态,社会风俗就会趋向败坏。道德伦理维持不坠,乃至向上的唯一动力是君子的自觉。依赖这种道德感的自觉,依赖具有“思”的能力的人对此能力的充分运用,克服物欲之蔽,君子将真正地向着尧舜的模范逼近。所谓君子,就是在较高程度上自觉地实践人性内在之善的人。
但是,君子个人的良心自觉与道德实践又如何能够改变风俗呢?《大学》提出了一个风俗变化、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格物,就是感通于物,为家国、天下的状况,尤其是其间的人的状况忧虑,而发愤有所作为。此作为的第一步就是致知,即孟子所说的“思”。由此君子首先致力于个体之诚意、正心与修身,随后,致力于影响家庭、家族、社区中的熟人,改善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由此也可以更进一步,通过讲学、为官等方式影响到陌生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国治、天下平。
由此可以看出,学术与“士气”的振兴是儒家人物提振道德、重建伦理、变化风俗、再造合理人间秩序的关键。曾文正公清楚地论说过这样一个过程:“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这不只是理论上的模型,历史上曾周期性出现过这样的事件: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论私德》篇中引顾亭林之历史论断说,东汉、宋代、明末的世风最美,就是因为这三个时代的士气最盛,士气则源于学术的自觉。比如,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了一代士人;王阳明开创讲学之风,促使士人相互激励,尤其是向普通民众讲学。值得重视的是,宋明儒向下努力,致力于社会重建,今天人们熟悉的传统社会的种种自治制度,均成形于此时代。
清末同样出现过一次士人重振道德伦理的运动,它是由曾文正公发动的。文正公弟子黎庶昌曾这样描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正是经由这一道德自觉,才部分地改变了满清野蛮统治导致的全社会深度腐败局面,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乃至于后来的新政和立宪运动正是在这一道德基础上才得以展开。如果没有这场道德自觉,以乾嘉间那种腐烂无力的士气是不可能有这些突破性的现代化努力的。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儒家能够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重建发挥正面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