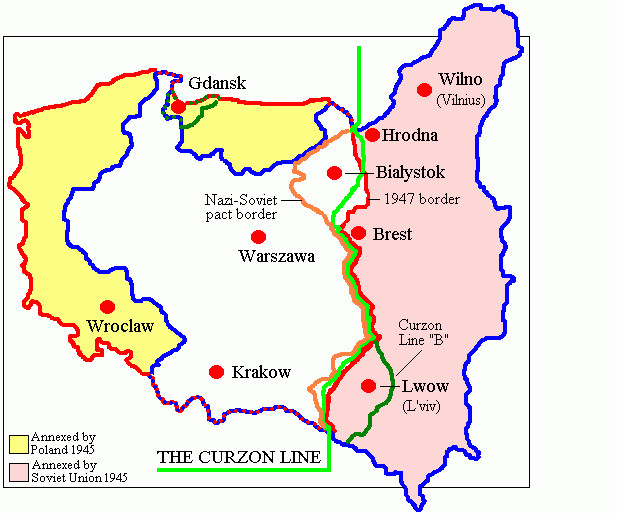《波茨坦公告》比《雅尔塔协定》影响深远,《波茨坦公告》决定了战后欧洲政体的未来。在雅尔塔,英国和美国对苏联的让步事后被西方政治家和评论家普遍谴责为“背叛”,尤其是背叛了反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当时所承认的,红军胜利挺进波兰,使斯大林为最重要的东欧国家所制定的计划成为既成事实。这使得“伦敦波兰人”在战后华沙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华沙政府将由共产党影响下的“卢布林委员会”控制。波茨坦会议进一步筹谋了战后的安排。波茨坦会议要求东欧德意志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化”边疆和斯拉夫、波罗的海诸国更分散的商业、农业、思想文化聚居区的德意志人——西迁重新定居,在很大程度上使欧洲的种族边界恢复到9世纪初查理曼帝国初建时的边界状态,一下子解决了最大的“少数族裔问题”,确保苏联在未来两代人的时间内控制中欧和东欧。
苏联随后拒绝配合1945年后德国占领区内举行的自由选举,这额外强化了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演讲时宣称的共产主义欧洲和非共产主义欧洲之间的“铁幕”。1918年的战后协议导致霍亨索伦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从中催生出自治的“后继国家”,使其政治局面变得特别多样化,1914年前这两大帝国曾经掌控欧陆的东半部。波茨坦会议则果断地简化了这种局面。在1945年后的欧洲,易北河以西仍然属于民主政体;易北河以东则实行单一的政治制度,由斯大林的苏联控制和支配。
1945年后,易北河以东地区被迫接受斯大林主义,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德国问题”,这个问题自1870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这并非解决了如何缔造持久和平的问题,无论是在欧洲,抑或是在全球。1943年在德黑兰,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意建立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发挥更大作用。1945年4月,联合国诞生于旧金山。联合国本是维持国际和平的工具,各成员国提供兵力组成联合国军,负责指挥联合国军的总参谋部受安理会(包括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5个常任理事国)管辖。苏联反对组建总参谋部,加上其后动用了否决权阻止维持和平的决议通过,很快削弱了安理会的权力。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或者被理解为布尔什维克重新致力于激发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或者更实际地被理解为以军事进攻威胁西欧反共国家,借以巩固1945年苏联取得的胜利,这种外交政策并没直接挑战联合国的地位。撇开赞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民主政变和1948年对柏林实行封锁,战后斯大林并没采取措施直接威胁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所缔造的欧洲稳定。他在其他地方挑战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菲律宾,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是在朝鲜半岛, 1950年6月,他支持共产主义北方进攻非共产主义南方。
事实上,1945年8月后,苏联让它在欧洲的军队复员,和美英同样迅速,如果并非同样彻底。到了1947年,红军的规模锐减三分之二;剩余军队仍然足以超出美国和英国占领军数倍——1948年莱茵河的英军只有五个师的兵力,巴伐利亚的美军只有一个师——虽然苏联的持续优势促使北美和西欧于1949年形成北大西洋联盟,但是这种差距并没使苏联冒险将领导权拓展到易北河以西。
对此存在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尽管苏联的外交政策粗糙严酷,但是这种外交政策由一种截然不同的律法主义加以指导,这种律法主义将苏联局限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所确定的势力范围。另一种解释是,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严格来说持续到1949年,但是其后十年间也发生了效力,阻止了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冒险。第三种解释,也是在争论中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是,战争的创伤压制了苏联人民及其领导想要再度体验的念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是令战胜国而非战败国相信战争的代价超过其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可以说,是让战胜国和战败国都相信这一点。自从法国大革命以降,“每个人都是战士”是先进国家组织军队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组织社会的原则,这一原则于1939年至1945年达到顶峰,这样做使这些国家承受了巨大痛苦,以致它们将发动战争的概念从其政治哲学中剔除出去。美国的战争损失最小,获益最多——1945年,战争使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强大——能够积攒足够多的国家认同去打两场规模小但损失惨重的亚洲战争,一场在朝鲜,一场在越南。就人力损失而言——如果不谈物力损失——英国历经战争而相对安然无恙,它仍然保有进行一系列小规模殖民主义战争的意愿,法国也会这样做——法国是另一个人力损失不太严重的国家。相反,纵然战后苏联向假想敌显示肌肉,但是却避开让其士兵直接冒险的武力对抗;最近,苏联闯入阿富汗,阵亡人数是美国在越南阵亡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似乎强化而非削弱了这种看法。自1945年5月以来,尽管195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征兵制度,但是没有一名德国士兵被敌人所杀,这样,死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日本是1939年至1945年最无所顾忌地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今受到战后宪法约束,规定无论任何情况下诉诸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都是不合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家都没愚蠢到宣布,打这场仗是为了“以一场战争终结所有战争”——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政治家所做的那样。然而,这可能恰是其持久的影响。
节选自《二战史》约翰·基根/著 李雯/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